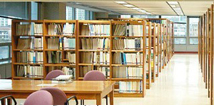第一章李清照家世
一、百脉泉边一人家
李清照父祖辈的籍贯叫作齐州章丘。到了北宋政和六年,齐州升为济南府,统辖今山东章丘、历城等五六个县市,因此称李清照为济南人也是顺理成章的,但有人把她的故居说成在历下柳絮泉则是讹误的。造成这种讹误并以讹传讹的原因,已有多种论著做过考证和说明见王学初《李清照集校注》第211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(以下简称《王集》);于中航《廉先生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》,《光明日报》1981年6月15日;陈祖美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·李清照评传》第38~41页,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(以下简称《李传》)。,如今人们已经达成共识,即李清照的原籍在今山东济南章丘明水镇。
章丘位当鲁中山水盘踞之地,北连黄河,南傍泰岱。它不仅历史悠久,更是北方罕见的稻香鱼肥之镇。这里河网密布、清泉淙淙,其八处胜景中,首屈一指的是“百脉寒泉珍珠滚”。章丘的百脉泉自古以来与历下的趵突泉齐名,且同出于泰岱地下水系。趵突泉的特色是泉源上奋,水涌若轮;而百脉泉则可谓泉涌如注,灼若明珠,冬暖夏凉,气候宜人,所谓“清境不知三伏热”是也。春来花红柳绿,夏至风清荷香,这是太平盛世时期章丘的近镜头。
当年在离它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水波浩渺的“莲子湖,周环二十里。湖中多莲花,红绿间明,乍疑濯锦。又渔船掩映,罟罾疏布。远望之者,若蛛网浮杯也”见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一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。不仅此湖贻人以鱼米之利,还有“虎牙桀立,孤峰特拔以刺天,青崖翠发,望同点黛”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。的华不注山秀峙湖畔,更能引发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名人的纵深之思。
在百泉喷涌、丛林掩映之中,有一处亦城亦乡、亦商亦农、尊教重学的集镇。此镇有一个闻名遐迩的特点,叫作三山不显、三水不露。所谓“不显”,就是在三个平缓的阜地上建成三处街道交会的十字路口,每个“十字口”就是一处繁华的商业网点,那里店铺林立,就势而建,人来车往,熙熙攘攘,故而有“山”不显;所谓“不露”,就是镇上有三泓水势可观的清泉,分别坐落在松竹茂密之处,又是在当地以诗书相传的三户人家的庭院之中,外人难得一见,故称“不露”。
这也是一个齐鲁礼仪之邦中的文明之乡。镇上有一户名声很大、又最受尊重的人家姓李。相传李家原先世居临淄城,所以其后人对那里很熟悉,也很有感情见李清照《上枢密韩公诗二首》:“嫠家父祖生齐鲁,位下名高人比数。当时稷下纵谈时,犹记人挥汗成雨。”“稷下”即是齐国的都城临淄(今属山东淄博市),又曾是人数众多的各学派荟萃、讲学议论之处。这些人才当时被称为齐之稷下学士,李清照的祖上当是这种文学纵谈之士中的佼佼者。。唐末避乱,移居乡间。对眼下居住的这方水土,李家世世代代各有建树和贡献。到了北宋中叶,这里几乎变成了人间仙境、世外桃源。几乎家家有白饭青蔬之食,清泉活火之饮。
当初方圆百里之中盛传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位来自他乡的太守,酷爱此间山川泉石之胜,遂生久留之意。由于太守政绩惠及下民,邦人亦欲其久留于此,唯恐不能长久。果然转年初春,诏命太守移牧北方。邦民、同僚恋恋不舍,临行饯别于林泉之中,太守举杯谢曰:“朔方得以安抚,我将复回终老于此。”太守移官后,乡民将他的诗作刻在石上,以慰相思之情。
李姓的当家人,虽然其名讳不被后人所知,但他的名望却口碑相传,令人肃然起敬。这位贤者后来成了我国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祖父。李家庭院中的“不露”之泉尤为清澈,泉眼有多处,日夜淙淙流淌。有一泉名很有讲究,这是后话。贤者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刚过而立之年,已有三个儿子出世。三个儿子都很可爱,最小的一个尤为出色,他就是后来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。李清照的祖父在为三个儿子命名取字时恪守古训“名以正体,字以表德”,取字要在十五岁,此外还要仔细体察天资秉性、喜好、所长,以为取表字之据。老二自幼性情谦和,敝欲字之“和叔”;老三眼下还是一个聪明活泼的顽童,但何以命“字”,尚待定夺。
二、“位下名高”的父祖
李清照作品中,涉及自己家世之处尚有“有易安室者,父祖皆出韩公门下,今(指绍兴三年)家世沦替,子姓寒微,不敢望公之车尘。又贫病……”见李清照《上枢密韩公诗二首》:“嫠家父祖生齐鲁,位下名高人比数。当时稷下纵谈时,犹记人挥汗成雨。”“稷下”即是齐国的都城临淄(今属山东淄博市),又曾是人数众多的各学派荟萃、讲学议论之处。这些人才当时被称为齐之稷下学士,清照的祖上当是这种文学纵谈之士中的佼佼者。“赵、李族寒,素贫俭”见李清照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(以下简称《后序》)。。这里的“韩公”是指南宋绍兴初年枢密院副长官韩肖胄的先辈。其曾祖韩琦在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为相,祖父韩忠彦在徽宗建中靖国为相。李清照的祖父和父亲曾得到过他们的举荐,故云“皆出韩公门下”。“韩公”曾是为朝野所敬、为“戎狄”所畏的很有威望的贤相,清照的父祖得到贤相的举荐自然是很荣耀的事。
不仅李清照,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也提到其家境贫寒。所谓“贫寒”既是相对的,又是指她的父亲和翁舅赵挺之的出身而言的。她说这些话时,其父已官至礼部员外郎,翁舅还做过宰相,地位并不低。但是与她的从执政到宰相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外祖父王珪相比,还是相形见绌的。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时,赵、李两家的社交圈大多是高官厚禄者。所以尽管她自谓贫寒,也不能理解为生活多么拮据,至多是不事奢靡,比较俭朴而已。
所谓“位下”者,当是指如今我们连名字都不得而知的她的祖父,其称为“父祖”,那是行文时连带所及的偏正结构,因为得以青史留名的礼部员外郎李格非,其地位不能说是很低的。话说回来,李格非的地位虽然不算低,但与他的声望、才学相比,位列五六品的礼部员外郎又确实是很低的。加之屡遭坎坷和贬抑,在此期间政治处境不必说,经济生活也难免于困厄。所以在李清照自谓其家世寒微的言辞中,恐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牢骚和不满。
追溯李清照的家世,是为了探索她的思想和作品的渊源所在。其佚名的祖父对她有何影响,已无确证;而其父的为人行事和前途命运,对她却是举足轻重的。
李清照的父亲名格非,字文叔,自幼俊迈出众,不尚虚名,注重经世致用之学,在当局还以诗赋取士时,他却撰成《礼记说》数十万言,遂于宋神宗熙宁九年登进士第。先调冀州司户参军(管理民户的低级官吏),在他任郓州教授郓州:今属山东;教授:掌管学校课试等事的职位不高的学官。时,“郡守以其贫,欲使兼他官,谢不可”。此事颇可玩味:“郡守”之所以想对李格非格外优待,很可能是因为此时李格非已成为朝廷要人王珪的东床,至少是很得王珪的赏识。李格非以公职人员不可以搞第二职业为由加以谢绝,一则表现了他的清正廉洁,二则也很可能觉察到“郡守”的“醉翁之意”。宋朝的官制比较严格,任期满三年后不能转官晋升,就得调任他职。李格非由地方小官“入补太学录”太学录: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所属学官,掌管执行学规,纠正并处罚犯规学生,同时协助教学。,自然是晋升无疑。据晁补之《鸡肋集·有竹堂记》所载,公元1089年五六月李格非为太学正。“学正”在国子监负训导之责,并佐助教学,地位在博士之下、学录之上。那么李格非“再转博士”当在公元1091年前后。大约公元1093年,李格非入做馆职馆职:以宰相为首的掌握刊辑经籍、搜求佚书等类职务,五六品的宫廷文职官吏。后,以文章受知于端明殿学士、礼部尚书苏轼,为“苏门后四学士”之一。
派系争斗在始于青之末时往往很微妙。元祐末年秋高太后去世、哲宗亲政,新派人物章惇、吕惠卿复官。或为罗织元祐大臣罪状,尝欲任命李格非为仅次于编修的“检讨官”。磊落清正、又对苏轼等元祐要人深怀感戴之意的李格非拒不就任,因而触犯了当局,被外放为广信军(今属河北)通判(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,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)。在广信军任上,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,即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,偶有应验时,便身价百倍,出必乘车,村俗之人为其迷惑。一日格非路遇此道人,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,揭穿了其奸计,用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,将其驱逐出广信军境。不难想见,这个个性鲜明,甚至令人意外的举动,在口碑相传中,对李清照会有着怎样重要的熏陶。
绍圣二年(1095),李格非被召回京,直至崇宁元年(1102),相继膺任校书郎、著作佐郎、礼部员外郎等职。这期间李格非的仕途极为顺遂。但此后不久,哲宗开始贬斥元祐大臣;徽宗继位,任用蔡京、赵挺之为左右相,对元祐重臣惩处加码——苏轼等已故者逐一追贬,对生者不仅一贬再贬,且罪及子弟亲属。李格非曾受到苏轼赏识而被株连,先外放为提点京东刑狱(于今山东一带掌管司法和刑罚的官吏),继而名列“元祐奸党”被罢官。虽然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谓传主卒年六十一,但其生卒之年本传中却没有明确记载。鉴于崇宁五年(1106),因太白昼见,大赦天下,诏毁元祐党人碑,除党人一切之禁,对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;又因“济南佛慧山有大观三年(1109)李格非题名”见于中航编著《李清照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1月版。,这不仅意味着此时李格非尚健在,而且被罢离京归于原籍后,当未再返京任职,而终老于“东山”东山:宋时称今天的山东为东山、东郡、东土等。章丘的清泉松竹之中;又因张耒曾为李格非撰写墓志铭,所以墓主当卒于张耒谢世的公元1114年之前夕。那么可以推断李格非的卒年就是在公元1109年至1114年之间。
李格非曾著有《济北集》见韩沈《涧泉日记》卷上。、《李格非集》五十四卷见刘克庄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。、《礼记精义》十六卷、《永洛城记》一卷、《史传辨志》五卷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。等。他一生不仅著作丰赡,其文还被认为“高雅条畅有义味,在晁(补之)、秦(观)之上,诗稍有不逮”见刘克庄《诗话续集》。“李格非之文,自太史公后,一人而已”见韩淲《涧泉日记》卷下。。上述诸作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,但数量仍是极为可观的,加之水平上乘,洵可成为李清照特有的思想库。但可惜的是,今天除极少数遗文尚见于残碑和数种载籍外,绝大部分早已佚失,文只有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和《廉先生序》一篇传世,诗只有完篇三首和一二断句留存,且散见于《墨庄漫录》《冷斋夜话》《宋稗类抄》《宋诗纪事》之中。
三、以文学进身的外祖父
迄今为止,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关于李清照外祖父系某人的直接记载,而对有关资料的记载又必须加以厘定和发明,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比如李清臣所撰《王珪神道碑》云:“(王珪)女,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……”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说李格非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孙婿;而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则云传主之妻是王拱辰的孙女。对《宋史》关于格非妻的记载下文再做具体分析,而它肯定了郓州教授李格非之“女清照,诗文尤有称于时,嫁赵挺之之子明诚,自号易安居士”。这样同一个郓州教授李格非,其妻是王珪的长女,其女名清照,王珪自然是李清照的外祖父。
王珪虽然是王准之子,但王准早卒,王珪是由其季父(叔父)王罕教养成人的。在《宋史·王珪传》中,王罕不仅与传主占有差不多的篇幅,而且被描绘得活灵活现。王罕,字师言,在他以荫封知宜兴时,那里多湖田,但不知哪里被水淹、哪里没淹,难以做到公平收税。王罕亲自到田间,用画图标明田地的高低,按实情收税,老百姓都口服心服。王罕对付“恶少”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,而且能使贫富皆受益。在他任职户部时,能够做到“为政务适人情,不加威罚”。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多年的冤案,被老百姓誉为神明,并受到朝廷的褒谕和嘉奖。看来王罕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实干家。而后来成为显贵的王珪的为人行事,与其季父王罕却有所不同。
王珪字禹玉,原籍成都华阳,后徙舒(今安徽安庆)。其曾祖王永,宋太宗时任掌讽谕规谏的右补阙,为官理事能使“民皆感泣……帝大悦”。王珪自幼奇警,语出惊人。堂兄王琪读王珪很小时所作赋后,赞叹道:“骐骥方生,已有千里之志,但兰筋(千里马)未就耳。”后举进士甲科,很快升迁为侍读学士,替皇帝起草重要诏书,其间不仅得到欧阳修“真学士也”的称赞,仁宗皇帝也非常器重他,赐予他贵重的文房四宝。英宗治平四年(1067),忽召王珪至蕊珠殿,传诏命其兼进读四方书奏的端明殿学士,赐予盘龙金盆,并谕告不仅要他在秘殿充翰墨之任,还将任命他在政府和枢府担任要职。英宗还亲告王珪说:昔时有人说你的坏话,朕今释然,一点儿也不怀疑你。神宗即位,王珪升为学士承旨。熙宁三年(1070),拜参知政事。熙宁九年,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元丰五年,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
元丰八年(1085),神宗患疾,王珪请立延安郡王为太子,后为哲宗。本年进王珪紫光禄大夫,封岐国公。五月卒于位,年六十七。特辍朝五日,赠金帛五千以办丧事。追赠太师,谥曰文恭,赐寿昌甲第。王珪以文学进至宰相,同辈无不推许。其文闳俊瑰丽,自成一家;朝廷大典策,多出其手,词林称之。他也很自许地称:“三朝遇主惟文翰,十榜传家有姓名。”
然而王珪也有口碑不佳之处,人谓自执政至宰相,凡十六年,无所建明。当时目为“三旨相公”,即上殿进呈,云“取圣旨”;皇帝表态后,云“领圣旨”;退谕禀事者,云“已得圣旨”。史称其容身固位,阴忌正人,以济其患失之谋。绍圣(1094—1098)中,有人在朝廷散布说王珪欲立雍王,于是得罪被贬,几个儿子也被革职。徽宗即位后,恢复其官封。蔡京当政又被剥夺谥号,政和(1111—1118)中又得恢复,有《华阳集》传世李清臣奉诏所撰《王文恭公珪神道碑》云,王珪有文集一百卷。。看来不仅王珪的著作和文学基因可能对李清照产生一定的影响,他卒后的升降也可能对李清照的命运有某种左右。除了这位一言难尽的外祖父,清照还有五位舅父、三位姨母。其中二舅父王仲端(又作仲山)又是秦桧的岳父,其女自然是清照的姑表姊妹。
在对李清照可能产生某种影响的人物中,还有一位王珪的堂兄王琪,字君玉,儿童时代即能作诗。他上奏请建义仓、罢鬻爵、兴学校等,为仁宗所嘉许,授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。入对便殿时,皇帝曾对王琪说:“卿雅有心计,若三司缺使,当无以易卿。”在他做江宁知府时,经常发生火灾,有的说这是鬼神所致,人不敢救。王琪设法很快捉到奸人并诛之,火患遂息。他曾做过扬州、杭州、润州等地知府,后以礼部侍郎退休,卒年七十二。王琪数知东南名镇,政尚简静。
四、生母,寿夭的相门千金
有一点必须首先说明的是:李格非之妻和李清照之母不能简单地画等号,只能说格非前妻系清照生母。
因为关于格非妻有二说:一是元朝脱脱等所著《宋史·李格非传》,谓传主“妻王氏,拱辰孙女,亦善文”。此说迄今仍被普遍采纳,其不确之处尚未被适当厘定;二是宋朝庄绰所著《鸡肋编》,卷中谓李格非系汉国公王准孙婿九人之一,则格非妻系王准孙女。早于庄绰的相同之说是前不久有学者引《王珪神道碑》史料名称、出处详见《文史》第三十七辑,中华书局1993年2月版。云:“(王珪)女,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,早卒。”王珪是王准之子,那么格非妻,不仅是王准孙女,还是宋神宗元丰宰相王珪的长女。对于谁是李清照的生母,上述二说不可能并存,李清照只能是王珪的外孙女,其母在她出生不久即去世;关于格非之妻,对上述二说,则不能视为非此即彼,实际情况当是王准孙女是他的前妻,前妻早卒后,又娶王拱辰孙女为继室(详情见下),故称清照生母是一位寿夭的相门千金。
对于王珪长女何时嫁与李格非,在没有相应史料为佐证时,难以准确判断,只能从对现有零散资料的串联中做些大致推测,以便于破译李清照的生平、心态及作品中的某些难解之谜。
如果李格非在熙宁九年(1076)登进士第之后,很快被同一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的王珪选为东床,那就有一定可能与新妇偕往原籍或冀、郓二州。看来格非很可能是在郓州教授任上与王珪长女成亲的,否则,与王珪和格非均为密友的李清臣,不当说王珪长女适郓州教授云云。作为于元丰七年降生的李格非的长女李清照刘克庄《诗话续集》云:“(李格非)其殁也,(张)文潜志其墓……志云长女能诗,嫁赵明诚。”,目前尽管仍然没有直接材料排除她生于汴京宰相府第的可能,而可能性更大的是降生在原籍章丘。但令人不胜遗憾的是,在她出世不久,其生母便离开了人世。

 2025年8月第4周书目
2025年8月第4周书目